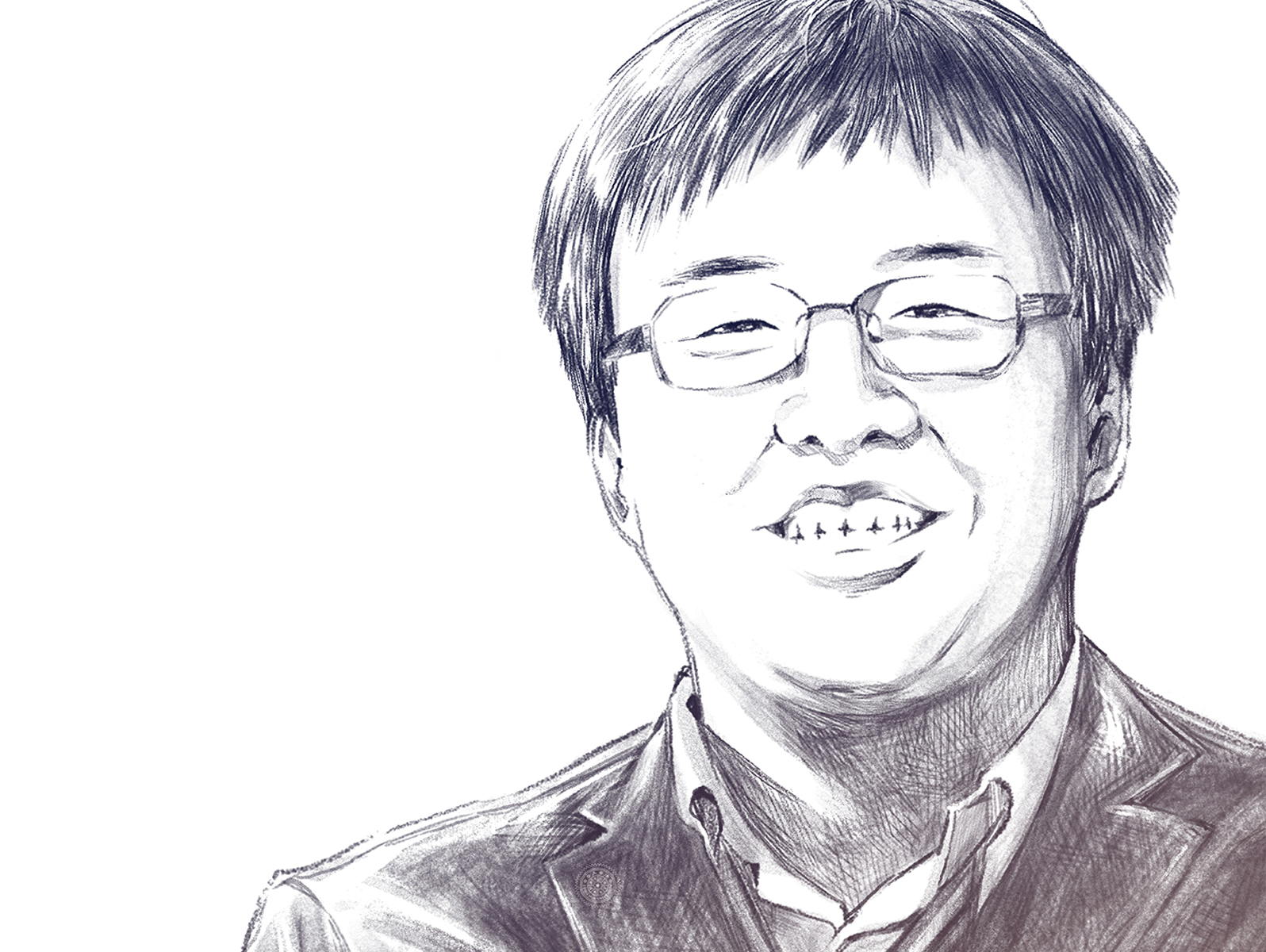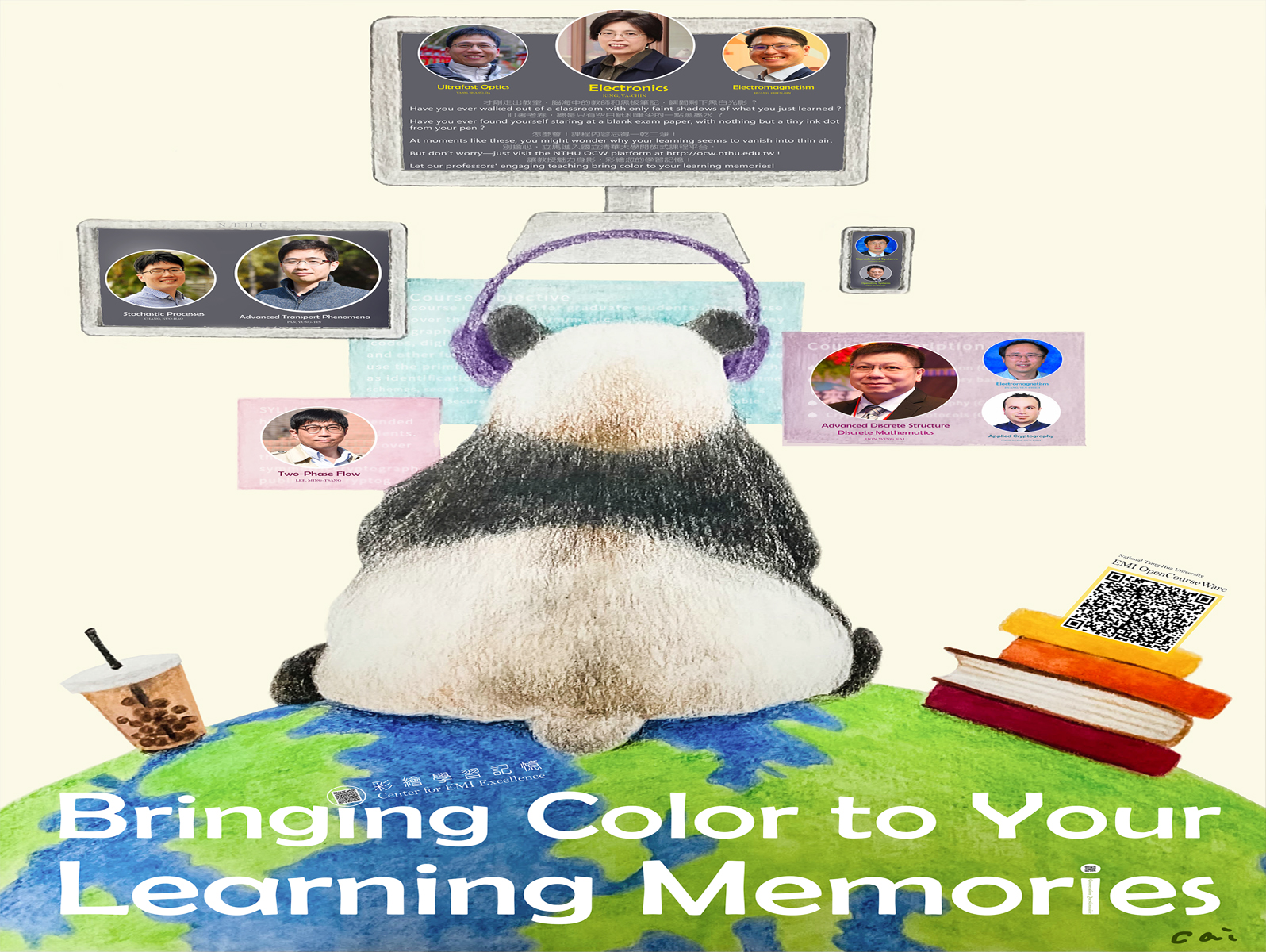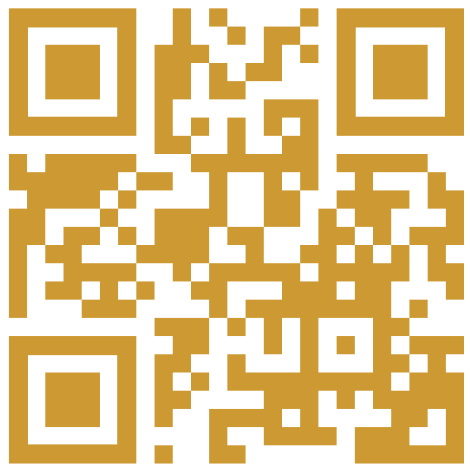朱曉海教授:《隋書‧經籍志‧敘論》東漢至西晉節補正
《隋書‧經籍志‧敘論》東漢至西晉節補正
朱曉海
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所教授
摘 要
以兩漢、六朝各時期中祕典藏量而言,西晉蓋居冠。如牛弘所言:此乃曹魏中祕既有書籍,「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所致。然而若按照《隋志‧敘錄》上文所述,東漢末兩京大亂,群雄逐鹿,書籍掃地皆盡,則魏、晉中祕書焉能驟興如是?緣是本文分為五個小節:首先指出兩漢已降典藏副本之制,是以東漢中祕藏書並未隨兵燹俱燬。其次指出當時雖然戰亂頻仍,私家依舊保有許多藏書。進而鼎革之前,曹氏已經陸續蒐求書籍。然後探討鄭默與魏中經的關係。最後嘗試解釋西晉中經書籍歸類兩項看似不得其解的原委。期盼藉此一斑,顯示:社會才是書籍歷劫猶存的關鍵。
關鍵詞:隋志、中祕、副本、鄭默、皇覽、汲冢書
前 言
後人撰述舊史,因有時、空之隔,非目睹親聞,既不能嚮壁虛構,必得仰賴所能見到的原始文獻及前人著述。由於個人行文習慣、時代風尚有別,撰述需求更不一致,於所採據者難免改寫。如陸績曾稱述張衡致崔瑗的信:
乃者以朝賀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己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1]。
范曄撰〈張衡傳〉時,則作:
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2]。
原信今雖不存,但兩相比較,後者改寫異動之鉅,無從掩。然而有時些微異動可能相去甚遠。如《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建武元年〉:
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
章懷《注》就指出:
《東觀記》、《續漢書》並無「右」字,此加「右」,誤也……酈元《水經注》云:「徐水經北平縣故城北,光武追銅馬、五幡,破之於順水,即徐水之別名也」。
一字之差,使得冀州中山國的縣(北平)變成幽州的郡(右北平),地理位置相去不啻數百里。
《隋書‧經籍志‧敘論》[3]多取自蕭梁阮孝緒〈《七錄》序〉[4]、楊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5],部分文字異動或所增益之處,也非無所本,然敘事、措辭有待補充說明者者,有待釐清諟正者。今取所述東漢至西晉一節以為例。先錄下有關文字:
歆遂總括群篇,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袠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以為《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西】京大亂,掃地皆盡。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錄(?)、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卷】,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
以為討論之資。
一‧兩漢中秘書有副本釋證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說: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6]。
班固自注:「入三家、五十篇」。對照《論衡》卷二九〈案書〉、〈對作〉兩度所云:
六略之錄,萬三千篇。
〈《七錄》序〉:
《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可知:今本《隋志》所言西漢中祕書數量有誤。「萬」前之「三」蓋後世傳抄時,涉後文而衍[7],未必是《隋志》原本即然。再看阮孝緒報導的南朝中祕書數量:
宋元嘉八年祕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有四袠、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二千三百三十二袠、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殿四部及術數目錄合二千九百六十八袠、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如果接受前引文、《隋志》對晉《中經簿》著錄書籍量的記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則以兩漢、六朝各階段的中祕書藏量而言,西晉居冠[8]。西晉中祕之書主要承襲自曹魏。據《三國志》卷二一〈劉卲傳〉裴《注》所引《廬江何氏家傳》:
明帝時,有譙人胡康……號為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禎【楨】康才何如……。
明帝在位不過十三年(227-239),從何楨在祕書丞任上[9],可推知:此事應在其中、末葉之交,上去東漢獻帝初平元年(190)方四十多年。這就引生一可探究的問題:洵如《隋志》所言,東漢中祕書於漢末兩京先後大亂時,「掃地皆盡」,曹魏中祕何以能於短期內已經充軔至可令人「博覽」,以廣見識的地步?
東漢藏書之處至少有蘭臺、東觀、宣明、鴻都數處[10]。「宣明殿在德陽殿後」,而德陽殿在北宮,故袁術入大內誅宦寺時,張讓等即「劫少帝及陳留王幸北宮德陽殿」[11]。「鴻都門,洛陽北宮門也」[12],故來歙等勸阻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時,「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而未幾孫程等迎立濟陰王被復辟,即在北宮德陽殿[13]。「南宮有東觀」,故曹褒請求「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14]漢儀。董卓「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掃地殄盡」[15],東觀、宣明、鴻都藏書固難倖免,然據《三國志》卷十三〈王朗傳〉裴《注》所引《魏略‧儒宗傳》:
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薛)夏為不得移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
可知:蘭臺在宮城外,未必被兵燹之禍。時任司徒、守尚書令的王允隨著鑾駕往長安時,「所收而西」之書籍「七十餘乘」,不論是否於南、北二宮焚燬前搶救所得,由於西遷「道路艱遠,復弃其半矣」。縱然後來沒有因為「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16],獻帝東返洛陽時,據《後漢書》卷七二〈董卓傳〉記載,先在弘農東澗與李傕、郭氾等追兵一場惡戰:
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
未幾,李傕、郭氾等再度來犯,欲將獻帝等劫回,使得東返隊伍不得不自陜縣北渡河以避。因為爭赴船者不可禁止:
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
書籍焉能保全?換言之,若賴西遷圖書東返,不啻緣木求魚。
《漢書》卷七四〈魏相傳〉:
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
即使所奏非封事,亦然。東漢中葉,江夏郡「上蠻賊事」,副本則至三公府。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17]。根據《漢儀注》,天下計書也是正本交付太史令,「副上丞相」[18]。天子頒發的詔令、冊書亦然。如開國功臣的簿籍「臧在宗廟,副在有司」,顏師古就說:「副貳之本又在有司」[19]。所以別需副本,自然是防止中間遭到竄改,以備有疑問、訟獄時,可核對勘驗。西漢景帝雖然曾給魏其侯竇嬰遺詔:「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大概因為疏漏,未將底本歸檔,以致在獄中的竇嬰據此上書求見,「案尚書」,不見,落得矯詔之名,「罪當弃市」[20]。顧慮到若僅有孤本,一旦遺失、毀壞,無復可紬讀者,同樣是重要因素,是以中祕書不可能沒有副本。西漢成帝時,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雖然因為王鳳作梗,未允,縱使如所請,所賜的也是既有或因此謄錄的副本;成帝賜給班斿的就是「祕書之副」[21]。從後來曹植過世,明帝下詔,一方面將以往彈劾、集議曹植罪狀,而收藏於「尚書、祕書、中書、三府、大鴻臚」的檔案「削除之」;另方面命有司「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22];荀勖等整理完《穆天子傳》,「付祕書繕寫」後,「藏之中經,副在三閣」[23],可見:官方典藏者,不論其性質是行政公文或蒐得的私人著述、圖書,均有副本,有時還不止於一。由此可推知:董卓西遷長安,欲絕
此由二事可覘。一,從明帝開始,命執事人員撰寫新莽之後的紀、傳、載記[24]。由於這個工程記錄的是東漢王朝的國史,只要東漢王朝一日未亡,就需要一階段一階段地撰寫下去,是以在安帝、桓帝年間又有兩度大規模的續修[25]。當時已總共完成了「百十有四篇」,並命名為《漢記》。最後一次集眾手「接續紀、傳之可成者」[26]在靈帝熹平中。據《史通》卷十二〈外篇‧古今正史〉所述:
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弃,舊文散佚。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初【和】以下闕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27]
楊彪這位參與熹平修史的成員暮年[28]仍在零星地撰寫。他工作的地點究竟是在許昌,還是後來移至洛陽,不得而悉,也無關宏旨,要緊的是:如果當初西遷時,曾帶走既有的《漢記》,根據上文所述獻帝東返時的狀況,楊彪續撰時,使用的不可能是從長安再攜返關東的既有《漢記》[29]。如果東觀所藏的《漢記》於西遷前,已在董卓兵燹中化為灰燼,就更顯示:楊彪使用的是南、北二宮祕閣外儲存的《漢記》副本。二,古文《尚書》連同其他的書自孔壁出,即歸孔家,所謂「悉得其書」[30]。孔安國整理完畢,孔家將此「隸古定」[31]本,連同原件摹寫本獻於朝廷,「遂秘於中,外不得見」[32],此所以張霸妄造百兩《尚書》,一出中祕本相較,其偽立見[33]。《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列傳‧呂強傳〉記載:
(李)巡以為
改動的是中祕本,非將中祕本抄出,以為私有,進而藉此立異。假使校書東觀者真有人將孔安國整理後的本子謄抄攜出,用的字體當是通行的隸書;官方或社會上講授古文《尚書》時[34],使用書本的字體應亦然,因為絕大多數的士人早已經無法辨識古文了。換言之,除了曾為杜林所有、傳給後學的漆書古文《尚書》[35],社會上根本沒有古文抄寫的《尚書》,而杜林傳下來的也僅一卷。王允收拾部分書籍,隨獻帝西遷時,即使曾將中祕所藏原件的摹寫本一併帶走,也已於獻帝等東返時亡佚。然而曹魏中祕必有西漢時期孔家所上的那個摹寫本或其副本,否則,正始年間刊刻三體石經的《尚書》時,古文部分將何所據?其來源顯然是東漢中祕原來所藏,又倖免於東京浩劫者。
這種中祕別有副本,以致某館閣中的書籍雖遭毀壞,許多書依舊存在,日後非無同樣的案例。「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36],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此所以王僧辯滅侯景之後,蕭繹將公、私藏書運回江陵時,連同「重本」,多達「七萬餘卷」[37]。其中原為公家典藏部分,去殘佚,恐也不下二萬餘卷。
二‧論東漢末大亂私家藏書猶存
從《漢書》卷八八〈儒林列傳〉: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
《後漢書》卷七九上〈儒林列傳‧孔僖傳〉:
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孔氏顯然於獻書同時自留一抄本。這並非特例。《太史公書》撰畢,司馬遷就明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38],底本傳於外孫楊惲[39]。虞翻完成《易》注,除了將一副本寄示孔融,另外以隸書,所謂「正書」抄了一「副」本「上」[40]孫權。
曹氏消滅袁譚之後,搜閱王脩宅,家「有書數百卷」。長安大亂後,蘇則與「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這些書籍的內容為何,無法得悉,但從蘇則「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按漢代規定,像他這樣尚未入仕者若應舉,是要課試章句的[41],則經書應該在內。「科禁內學及兵書,而(吉)茂皆有,匿不送官」[42],當時已屆建安二二年(217),則某些人未受兵燹影響的藏書還包括禁書。蘇則、吉茂在本鄉都是「世為著姓」[43];王脩起家即能在本鄉北海國被辟為主簿,應當亦然。既然他們家中都能有書籍,則陳留望族出身的蔡邕[44],益以後來學、宦的方便——「師事」的是學界鉅子「太傅胡廣」,又曾「校書東觀」[45];董卓為了籠絡他,還曾假皇命賜書給他:
《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奏議》,合成二百一十二卷[46]。
則家中有豐富藏書,乃是事有必至者。眾所周知,蔡邕曾公然表示:「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王粲[47]。說這話的時候,蔡邕已隨獻帝、董卓西遷至長安。而且從張華《博物志》的記載:
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邕所與書悉入(粲族子)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48]。
及張湛〈《列子》序〉: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49]。
不但可知:蔡邕並非憑空許諾,而且顯示:兩京大亂,固然波及許多地方,然而不少郡國大姓的私人藏書並沒有全部被燬壞。非但如此,從《三國志》卷十一〈袁渙傳〉裴《注》所引《袁氏世紀》:
(呂)布之破也……太祖又給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50]。
則縱使戎馬倥傯之際,軍中仍有書籍隨行,以致可成為戰勝一方的擄獲物。
在這種背景下,再來看曹丕的自述:
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51]。
以及魚豢的轉述:
(曹植)與(邯鄲)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52]。
就會覺得並無夸飾之處了。試想:以曹氏曾祖(大長秋、費亭侯曹騰)、祖父(太尉曹嵩)兩代的地位,加上曹操「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解方藥」[53],並親自課子[54],家中當更會有豐富藏書。無怪乎在這樣良好環境下成長的曹植才「十歲餘」,就已經「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55];曹丕能與左右「妙思六經,逍遙百氏」[56],真正達到遊於藝的境界。
三‧曹魏蒐求書籍概述
《三國志》卷二〈文帝紀〉記載:
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根據卷九〈曹爽傳〉裴《注》所引《魏略》:
延康中,(桓範)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
卷二一〈楊俊傳〉裴《注》所引《魏略》:
受詔撰《皇覽》,使(王)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57],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
可知:在建安二五年、即延康元年(220)之前,必定已有相當可觀的書籍供抄撰,否則,不會貿然啟動這項工程,日後也不可能成此巨構。那些書從何而來?除了洛京館閣遺存者、曹家自己的典藏,如上節所示:社會上始終存在的書籍也可提供資源,而那些書籍還不限於經傳、諸子。管輅生於獻帝建安十四年(209),高貴鄉公正元三年(256)卒,「年四十八」。他固然「道術神妙,占候無錯」,據他弟弟管辰說:
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
他學《易》筮、「仰觀」天象、「鳥鳴之候」等,在其就學,所謂「黌上」階段[58],不會超過二十歲:明帝太和二年(228)。擁有那些書應當也在這段期間。《易林》乃兩漢舊著,固不待論,餘者恐亦然,因為此時上去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戰才二十年,這些書若是入魏以來的新作,社會上不大可能那般普及。是以編撰《皇覽》時,若要採擷術數這方面的文字,也非難事。
建安十八年(213)「魏國初建」,袁渙勸曹操:
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59]。
既言「大收」,言下之意,似前此已經陸續收藏。目前可確定的線索有二:《後漢書》卷八四〈列女列傳‧陳留董祀妻傳〉記載:
(曹)操因問曰:「
其次,《三國志》卷六〈劉表傳〉裴《注》所引《英雄記》說:
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既然以最後定本自詡,前提必須是東漢數量龐大的各家章句大體齊備,才談得上進一步「刪剗浮辭,芟除煩重」,凸顯出這些新章句具有「用力少而探微知機者多」[61]的成效。從〈劉鎮南碑〉所述:
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舊籍,必集州閭。
劉表搜置的書籍不限於經生之作。建安十三年荊州牧劉琮歸降時,荊州的藏書應當都隨之北上。杜預曾表示: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餘家……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62]。
「《春秋左氏條例》五萬言」乃潁容「避亂荊州」[63]後所著。此書若非隨曹操、劉琮等入北,日後杜預從何得見?由此可知:魏氏「采掇遺亡」發韌甚早,不待鼎革「代漢」之後。
建安二十一年(216),王粲「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64]。同年,因「疾疫」,「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隔年,當時尚是魏王世子的曹丕與吳質書信時,已言:「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65]。待即位後,《後漢書》卷七十〈孔融傳〉說:
魏文帝深好(孔)融文辭,每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王粲未卒之前,曾與司馬朗等論是否「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文帝善朗論,命祕書錄其文」。明帝已降,曹植過世後,官方主動收錄他平生的作品凡百餘篇;任嘏死後,他的故吏將其所「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言」奏呈,「詔下祕書」;王肅「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66],皆列於學官,曹魏中祕當然也會典藏。是以若說:建安末以至曹魏時期士人的著述先後入中祕,當非近誣。
四‧鄭默「始制中經」辨
〈《七錄》序〉說:
魏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
《隋書》卷四九〈牛弘傳〉本此,僅將「謂為」易作「美其」,使稱許之意更為明晰。對察同屬唐初史館所修的《晉書》卷四四〈鄭袤傳附子默傳〉:
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此蓋根據王隱《晉書》:
刪省舊文,除其浮穢,著魏《中經簿》[67],中書令虞松謂默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68]。
不論行文繁簡,似乎都在表示:許多流傳至後世的書籍都曾經鄭默刪改,並非劉向、歆父子整理後的「舊文」原貌,與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69]同類。洵如是,殊屬駭人聽聞。按:〈《戰國策》敘錄〉:
除復重,得三十三篇……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70]。
〈《管子》敘錄〉:
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71]。
〈《晏子》敘錄〉:
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72]。
〈《列子》敘錄〉:
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73]。
同一書,整理中祕書者所見有各種抄本,或全或殘,此有彼無,需互補;彼此共具,則須「除復重」,「除復重」即「刪」,重言之,即「刪省」。傳抄多誤,字句或脫衍,須更正,而後「定著」,簡言之,即「定」。二者合言之,即〈《七錄》序〉、《隋書‧牛弘傳》所說的「刪定舊文」。由此可知:鄭默與劉向、歆父子當年所作者一致。「舊文」指當時藏於曹魏中祕或得自外間的各種抄本。以此整理、訂正過的「新書」與「舊文」相較,迥出乎上,所以說「朱紫有別」。
《隋志》捨鄭默這項工作弗敘,卻曰「制中經」,此非特阮孝緒、牛弘所未言者[74],且與所本之王隱《晉書》亦不盡同,其間原委或可探討。
建安末,魏國初建,置祕書郎,但此時的任務乃掌機要、起草文書,所謂「典尚書奏事」[75]者,故《三國志》卷十四〈劉放傳〉言:
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
曹丕將「掌機密」的單位名稱改為中書,但原單位的名稱:祕書則保留,回復東漢末之制,「掌藝文圖籍之事。初屬少府,後乃不屬」[76]。此專典書籍的單位最高長官曰祕書監,下有祕書丞,再下方為祕書郎。其業務,《初學記》卷十二〈職官部下‧祕書郎第十一〉所錄《晉令》曰:
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覆校殘闋【闕】,正定脫誤。
其人數,《通典》卷二六〈職官八‧祕書郎〉記載:
晉祕書郎……亦謂之郎中。武帝分祕書圖籍為甲、乙、丙、丁四部,使祕書郎中四人各掌其一。
此誠屬晉制,然晉多沿魏制,縱使曹魏時期書籍尚未如後世四部分類,曹魏祕書郎當也不止於一人[77]。《北堂書鈔》卷一百一〈藝文部七‧刊校謬誤二十五〉所引荀勖〈讓樂事表〉云:
臣掌著作,又知祕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促。復兼他職,必有廢頓者也。
此表蓋作於泰始末[78]。將西晉王朝建立至此始入中祕者,如平蜀後陸續所得[79],扣除,曹魏中祕至少當已有六、七萬卷,如此多的書籍,豈一位祕書郎可肩荷?《三國志》卷二八〈鍾會傳〉記載:
正始中,以為祕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
裴《注》所引鍾會為其母張氏傳中云:
正始八年(247),會為尚書郎。
鍾會任祕書郎自在此之前。《晉書》卷四四〈鄭袤傳附子默傳〉敘默仕宦履歷,「起家祕書郎」後,接著就說:
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長史。
鄭默「太康元【九】年(288)卒,時年六十八」,是生於曹魏文帝黃初二年(221)。以當時一般士族子弟的狀況而言,大多二十上下起家,則從鄭默於齊王正始三年(242)前後入仕,是鍾會必曾與鄭默同事,明顯可見:按曹魏編制,祕書郎非一人。揣度王隱《晉書》所以會有鄭默「著《中經簿》」之說,可能因為伐蜀事在曹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尚書考功郎乃吏部尚書的下屬,與祕書郎同為六品[80],足見:鄭默前此一直未昇遷,而且顯然沒有其他逸聞墜簡可供王隱等《晉書》撰寫者填補,則鄭默在祕書郎任上竟長達二十來年!這當然極不尋常[81]。王隱等或許因此推斷鄭默當有某些重要作為,故那段時間均棲遲祕閣。《隋志》大概對此存疑,故僅言「始制中經」。檢視初唐史館所修諸書「始制」的詞例,如:
始制大臣聽終喪三年。
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
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始制凡朝會應登殿坐者,劍履俱脫[82]。
應該是規定、成為一制度之意。鄭默替曹魏中經制訂了什麼規範,不得而悉,但玩索上文「除其浮穢」,或指劃定中祕典藏範圍等。所以作此揣度,因為兩漢的祕書範圍甚廣。《漢書》卷六八〈霍光傳〉:
(霍)山又坐寫祕書,(霍)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
從上文看,乃封奏之屬;《後漢書》卷四二〈光武十王列傳‧東平王蒼傳〉:
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章)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
從下文看,乃僊方之流[83];《文選》卷二〈賦甲‧京都上〉所收張衡〈西京賦〉:
乃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
據薛綜《注》,乃「醫巫厭祝之術」。至於緯、候等,更屬祕書[84]。如果《隋志》對於《中經簿》典藏內容的部類概述無遺漏,則上述漢代的祕書或有不少見摒於外。無論如何,鄭默恐怕未嘗撰有分類意義的簿錄[85]。
《晉書》卷三九〈荀勖傳〉說:
武帝受禪……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86]。
可知: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的「新」乃針對兩漢舊有目錄而言,因劉、班等既有的六種分類已不符當時書籍狀況。若從荀勖所作的這目錄本身而言,何新之有?是以南朝至唐的學人即逕言《中經簿》[87]。以為「簿」前必標明「新」字,非通方之論。
〈荀勖傳〉又說:
及得汲冢古文竹書,詔勖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
汲冢書於咸寧、太康之際方面世[88]。其中有《穆天子傳》。此書後世善本前有進呈天子的敘文: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勖、領中書令、議郎、上蔡伯臣矯言:部[89]祕書主書令史譴勳、給祕書校書郎中張宙、郎中傅纘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訖,並第錄……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祕書繕寫[90]。
辨識、「校」、「寫」非一時可「訖」,則《中經簿》全部完成可能已屆太康中期,但不可能晚於太康十年(289),因荀勖於是年十一月過世[91]。上去西晉初已二十多年,足見:替當時中祕書整理一適用的目錄費時之久。
五‧《中經簿》於《皇覽》、「汲冢書」
歸類源由蠡測
前賢認為《中經簿》書籍歸類「有不可解者三:一,兵書與兵家何異?二,《皇覽》何以與史記並列?三,汲冢書何以不入丙部而附於丁部」[92],第一點誠難臆度,後兩點則或可說。
《皇覽》既然是「包括群言,區分義別」[93],或者說「以類相從」[94],令人很自然地認定《皇覽》是類書。類書型態多樣。歐陽詢說:
前輩綴集,各杼其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95]。
好似《皇覽》與《華林遍略》型態一致,詳觀前者的佚文,可發現有幾項特點。一,《皇覽》固然是「集五經、群書」而成,卻用自己的話重述。從古書中抽取出來的詞句、段落是作為論述的證據。例如《史記》卷二〈夏本紀‧太史公曰〉《集解》所引《皇覽》:
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壙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裘三領,桐棺三寸」;〈地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群鳥耘田者也[96]。
《越傳》云云是用來支持「會稽山本名苗山」的論述,並補充說明易名的原由。稱引《呂氏春秋》、《墨子》等,則是進一步發揮《越傳》所記禹節葬之說。二,正因為《皇覽》是綜合幾樣材料重述,有時會掩去出處,以利行文。例如《太平御覽》卷五六十〈禮儀部三九‧冢墓四〉所錄《皇覽》:
秦始皇冢在驪山之古驪戎國……其山陰多黃金;其陽多美玉,謂藍田是也,故貪而葬焉。并天下,徒七十餘萬人,穿入池,洞三泉,而致椁。宮觀奇器珍怪諸物藏之。令一匠人作機弩,人有近穴,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金銀為鳧鶴。機關轉相斡旋,終而復始。上具畫天文,以人魚膏為燈,度久不滅。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眾。恐工匠知之,殺工匠於藏中,因閉羨門,復土樹草木,以像山。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
「并天下」至「像山」一段無疑取材自《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縱使《史記》有更早的文獻依據,而為《皇覽》編撰者所見,按後世類書模式,也當標明何書,《皇覽》卻未然。又好比在曹植〈與楊德祖書〉「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這節後,裴松之下按語:
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97]。
即因《皇覽》不著出處,甚至可能添了點材料,他不敢確定曹植當時是否必然根據〈魯連子〉,這才導致注重行文省淨的裴氏[98]不得不辭費,再說「亦見《皇覽》」。三,論述著重的是編撰者的見地,所以有時會解說看似矛盾的現象。例如:「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與「山陽郡鉅野縣重聚」何以都有蚩尤冢,那是因為蚩尤在涿鹿戰死時,「身體異處」,後者是其「肩髀冢」;明明是「呂不韋冢」,何以卻名為「呂母冢」,那是因為夫妻同穴,「不韋妻先葬」[99]使然。有時會駁正,例如:
好道者言黃帝乘龍升雲,登朝霞,上至列闕倒影,經過天宮。天體如車有蓋,日月懸著,何有可上哉?
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
四,對於無甚大把握的,則保留異說。例如:
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
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五,引述的材料不限於古書,經常訴諸古老口耳相傳者,所謂「民傳」、「民傳言」、「人以為」。甚至利用出土文物以進一步確認。例如:
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鮦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頹壞填壓,不得發也[100]。
是以若持《皇覽》與《華林遍略》的殘文[101]相較,兩者固然都不節錄詩、賦等各類「文」,但仍相去甚遠,前者既不似後者規矩地標明出處;後者也不似前者會援引口述史料。若持與《意林》、《群書治要》等單純的書抄相較,也絕不類,因為《皇覽》是在分「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的架構下,選取、運用材料,構成的論著合集。或許正由於《皇覽》這種特殊體制,故在南朝被視為自成一流,不乏以此為準者:
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
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
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陸)罩與群賢並抄掇區分者數歲……以比王象、劉邵【卲】之《皇覽》焉[102]。
其實,最切要的是:曹丕可能如何看待自己下令修撰的這本書?從此書鎔鑄既有的材料撰成,材料範圍「兼儒、墨,合名、法」,「無不貫綜」[103],復題名《皇覽》:皇,大也;覽,觀也[104],取義《周易》卷三〈觀‧彖〉:
大觀在上……下觀而化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可見:曹丕顯然欲將此書與秦之《呂覽》、漢之《淮南鴻烈》鼎足而三,甚或凌駕二者,則《隋志》將之歸於子部雜家類,堪稱順適。然而正如章學誠所言,真正的雜家乃是「雜於眾,不雜於己,雜而猶成其家者也」[105]。即使等而下者,整本書的思想不成系統、見解淺俗,但它們與「入道見志」[106]者之間,僅是純駁、深淺之別。極可能在荀勖眼中,《皇覽》雖然以自己的口吻行文,駕馭古書中的材料以及故老傳言,時而夾有自己的研究見解在內,但仍被認為其本質乃資料彙編。以近現代的話來說,即史料,不過是其中剪裁良好、鎔鑄有方者。既然如此,當然應歸諸丙部。
「汲郡汲縣」所出「藏在祕府」的「古書」「大凡七十五卷」[107]。世俗認為:《中經簿》將汲冢書歸於丁部,乃出土未幾,性質辨識尚未取得共識下的權宜之計。姑且不論持此說者全然未反省:這是在已認定汲冢書歸於丁部不當此前提下的解釋,但這認定實乃道地以後律前的觀點,因為從形式邏輯而言,將前提改換為承認此舉有別裁心識,是一更具有理論效力的選項。更要緊的是:此說明顯違背史實。《晉書》卷五一〈束皙傳〉分別概述了各書的性質。如「《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國語》三篇論晉、楚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108]。今本《晉書》乃貞觀二十(646)重修[109]。當時汲冢諸書泰半已亡,根本無從得悉它們的內容大要,顯見史臣根據的是其重修主要底本:臧榮緒《晉書》[110]。然而臧書豈能憑空撰述?自然是轉述自前此的干寶《晉紀》、朱鳳《晉書》之儔[111]。層層後退,荀勖等人奉詔整理汲冢書,初步有頭緒後[112],向晉武帝的回奏才是這段汲冢諸書概述的原始依據[113]。換言之,荀勖等人對汲冢所出各書性質早已了然。是以真要按一般看法歸類,有何可躊躇之處?捨此不圖,仍以「汲冢」作為一子目[114],可見:在荀勖的觀點中,此等竹書某些部份固可歸於甲、乙、丙之部,然而某些部份有某種共通特質,宜與詩、賦等並列。試觀汲冢出土某些書的內容,如:
《穆天子傳》五篇[115]乃唯一完整見存者,不論其地理距離,或遊歷節目,如「見帝臺、西王母」,都令人瞠目結舌。
《紀年》十三篇所記大事與經、傳「大異」,如云:「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誠然,今日看來,《紀年》的這類記載可能較正確;近現代學人也力圖考證《穆天子傳》的內容多可徵實,但不能忽略晉朝當時讀者如何看待它們。郭璞以《紀年》支持《穆天子傳》的內容,顯示先前載籍中有關穆王遊行天下之說屬實,譙周《古史考》「著其妄」,殊屬不當[116]。再藉此「潛出于千載,以作徵於今日」的作品,來類推《山海經》的可信度,世俗不應「怪所不可怪」,豈非正因在「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117]這點上,三書同類?
〈師春〉一篇內容不但「抄集」「《左傳》諸卜筮」,而這部分正是後世認為《左傳》弊病所在,所謂「《左氏》其失也巫」,「謂多敘鬼神之事,預言禍福之期」[118],而且據宋人看到的本子,可能還援引了不少星野、律呂、卦變來疏證[119]。
「《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120]。
「《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鄒衍撰有《終始》之書、〈主運〉之篇[121],對照《史記》卷十三〈三代世表‧敘論〉,可知:乃歷譜一類作品。戰國以來就已經被目為「怪迂」「不經」,令人「懼然顧化」[122]。
「雜書十九篇」中的古文《周書》逸文尚見一二,如越姬以死鳥將姜后所生之子掉包,遭冥誅,於他界遭周先王嚴譴,七日後還陽,透露實情[123],也是子不語一類。
汲冢這部份的書予人的印象,一言以蔽之,正如整理單位總負責人荀勖所說:「其言不典」[124]。《尚書》卷十四〈康誥〉: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卷十七〈多方〉: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偽孔《傳》均以「不常」訓解。不常也就是非常可怪,所以杜預對這七十五卷的汲冢書直白地評論:
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125]。
其性質與志怪作品非常相近。古代的集部與近現代所說的文學作品不盡重合,《文史通義‧內篇》卷一〈詩教上〉說得好:
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
但集部確實以文學作品居大宗。文學作品內容需要有虛構的成分;手法經常會採取夸飾;期盼給予讀者的印象乃新奇。在這些方面,「汲冢書」與文學作品有頗多相通之處。既然如此,將之與賦、詩同置於一部,可謂正得其宜。車永論及陸雲那封夸飾鄮縣自然、人文條件俱佳的回信,認為筆法、內容簡直就像在寫篇賦的時候,就是以〈二京賦〉、〈南都賦〉與《山海經》、《異物志》相提並論,認為它們共通的特點是:「有其言,能無其事」[126]。與劉知幾所述「世人」對「汲冢書」的看法:「無其證」,「多不之信也」[127],若合符契。由於《隋志》認為「《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128];將鬼物奇怪之事視為另類存有的活動,這才將《紀年》等作品分別歸類於史部的古史、起居注、雜傳等子目下[129]。
不同的人對書籍性質的觀點有別,乃常態。此所以劉、班將《太公》、《管子》收歸道家,《隋志》卻將二者分別納於兵、法[130];一般將《戰國策》置諸史部雜史類,晁公武卻認為乃子部縱橫家之言[131]。執流俗成見,以論部別類居,實不足言辨章學術史,徒貽笑於章學誠等大雅。
結 語
隋文帝「素無學術」,「不悅《詩》、《書》」[132],卻極度迷信讖、緯。牛弘為了鼓動他開獻書之路,甚至將秦朝「墳籍掃地皆盡」與國祚短促比附為本末關係,不惜說出「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這種聳動天聽的話[133],並以「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以顯示「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既然遊說對象是皇帝,敘述焦點自然落在歷來中祕書的聚散上,是以所說的五厄適用範圍主要限於中祕。為了加強政治盛世與文教盛世唇齒相依的說服力,時不免難免夸飾。好比:新莽末年,長安遭赤眉之禍,自然不利於圖書的保存,但「光武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134]。假設當時運載的內容有一半是各類官署檔案,將這部分去除,一輛車裝十卷簡牘,已有一萬卷,此所以《漢書‧藝文志》與《七略》著錄的數量相去無幾,何嘗「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撰寫《隋志》之際,已無當時背景,未循〈《七錄》序〉較平實的陳述,猶多據牛弘之辭,僅小變之。管見所及,當補充說明,並釐清諟正者凡五:一,東漢末,兩京大亂,南、北二宮中的圖書確實先後都燬棄了,但洛下的副本並未隨之「掃地皆盡」[135]。二,縱使官方書籍的正、副本俱亡,社會上仍有可觀的藏書,曹操以及與他有「管、鮑之好」[136]的蔡邕即箇中著例。三,曹魏「采掇遺亡」,早在建安年間已開始,不待「代漢」之後。四,牛弘等以「刪定舊文」概述鄭默當時在魏中祕的工作,措辭固然欠明晰,易滋改變既有書籍實際內容之嫌,而實際不過是整理同一書的不同抄本,但《隋志》將之易為「始制中經」,愈發不清晰,工作實際內容至多是劃定書籍收錄的範圍。五,《中經簿》將《皇覽》、汲冢書分別置於後世所說的史部、集部下,與《隋志》代表的後世主流看法迥異,《隋志》既未辯駁,也未說明其所以然,竊以為《中經簿》如此歸類持之頗有故。上述五點中,最當措意者乃第二點。
王儉所做《宋元徽元年四部書目錄》,不過四卷,可是並私人藏書而計,所做的《今書七志》卻高達七十卷[137]。蕭梁天監四年文德殿四部圖書二千九百六十八袠、二萬三千一百零六卷。〈《七錄》序〉說:
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
據阮孝緒統計,釋、道以外當時見知的典籍共「八千五百四十七袠、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比官方藏書幾乎多一倍[138]。蕭繹將自己原有,連同平侯景之後,從建康公、私兩方面蒐集來的,共「十餘萬卷盡燒之」[139],當時擔任西魏南征部隊元帥府長史的唐瑾仍能「得書兩車,載之以歸」[140]。周師入鄴,「先封書府」,但身為伐齊前驅大總管的王傑照樣能「車載圖書」[141],帶回私宅。南、北這兩個案例充分顯示:不論官方藏書或燬或全,私人藏書的命運不必然與之同步。政治問題引生的戰禍固然會波及社會上的藏書,例如:秦末大亂結束後,伏生回到故里,求其藏書,就「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142];永嘉風暴時,張嶷、傅敷等逃奔江南,原來攜帶的珍愛書籍被迫於中途捨棄殆盡[143],然而書籍能否存續,主要還是有賴社會。否則,歷代官方開獻書之路時,新近撰寫者毋論,那些早先的書從何而來?《隋志》撰者同樣清楚,但終究格於君領導民的傳統立場,將社會收藏方為書籍命脈所繫這點壓縮。
《後漢書》卷四九〈王充傳〉記載:
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
沒有一定的讀者市場,牟利的商人不可能將書籍當作販「賣」品之一。如今既有書肆,就可見社會上對書籍有一定的需求量。而且從下文看來,還不限於日書、命相等通俗性書籍。此所以貧寒的士子可以「傭書」[144]自養養人,並藉此機會讀書。印刷術沒有發明之前,書籍流佈的程度自然遠不如後世,因此會強調記憶。某些人這方面的潛能固然格外豐沛,例如:荀悅於「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楊脩在宴席上,以曹操所撰兵書示秦松,「松一看便闇誦」、王粲讀道路旁的碑文,當下「背而誦之,不失一字」[145]。縱使記憶的潛能一般,不佳的境遇也能讓這方面的潛能充分被激發。彊記與博學因此出現了連帶關係。是以讀過或原來擁有的書雖然消亡,仍能重新寫出。蔡琰即其著例。像陸倕年少時,「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146],還只能算小巫。對於一般士人而言,中祕確實有許多未見未聞之書,是以左思「求為祕書郎」;風痹的皇甫謐「自表,就武帝借書」;張纘在祕書郎任上,「固求不徙」;蕭大圜由於少年時期即遭動亂,雖然四歲能誦〈三都賦〉,經學通明,直到北徙宇文周之後,因入麟趾「祕閤」,才得見其祖「梁武帝集四十卷」、其父「簡文帝集九十卷」[147]。然而並非每個人都有機會在中祕任職;向皇家請求籀覽秘書獲允,更屬難得,轉不如向同屬一階層所認識的人借閱謄寫。桓譚向班斿借《莊子》、李權向秦宓借《戰國策》[148],雖然都未果,但從舊史對於許慈、胡潛因為爭勝,「書籍有無不相通借」[149],採用的是責備的口吻,可知:肯出借才是常態[150]。綜言之,是在社會上對書的需求與珍愛、子孫對祖先作品的尊重與護持、學習過程強調記誦、博物多識的價值位階愈來愈高等等因素的匯集下,導致世人階層保存了各種書籍,因而在中祕書遭受重大虧損之後,方能藉由社會的資源再度充實。牛弘所說:「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乃為了刺激隋文帝而發,豈是應然?《隋志》撰者因襲此論調,實悖乎歷史事實。
(發表於《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總第16期,2010年12月)
Supplement and Correction to the Eastern Han to Western Jin Section in the Preface to “Jingji zhi” of Sui sh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royal library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was unrivalled in the volume of collection compared to those of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As Niu Hong牛弘 noticed, it is because the books collected by the royal library of the Cao Wei dynasty were inherited by the Jin. However, since all the books, according to Xulu敘錄 of Sui zhi隋志, were destroyed as the result of the riots breaking out in the two capitals in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how could the Wei and Jin royal libraries possibly thrive in such a short time? The current paper answers this question in five sections. First, 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a book copying system had been established since the Han dynasty, and thanks to which the collection of the royal library was saved from conflagration. Second,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private collection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books preservation. The third section shows that the Cao family had begun sought for books since as early as before the change of the dynasty. The following section discus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Zheng Mo鄭默 and Zhongjing中經 of the Wei dynasty. The last section tries to explain two enigmas in book categorization of Zhongjing of the Western Jin. By the above analysis, the paper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e following fact: it was the society itself that was the key to protecting books from destruction.
Key Words : Sui zhi, royal library, copy,
[1] 陸績:〈述玄〉,范望注:《太玄經》,《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3冊,頁4。
[2]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以下簡稱《後漢書》),卷五九〈張衡傳〉,頁677。
[3] 以下引文凡出自長孫無忌等:《隋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三二〈經籍志‧敘論〉,頁468-470,者,不復一一標明頁碼,且概簡稱為《隋志》。
[4] 道宣:《廣弘明集》(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卷三〈歸正篇〉所收阮孝緒:〈《七錄》序〉,頁37-42。以下凡出自此序者,不復一一標舉頁碼。
[5] 《隋書》,卷四九〈牛弘傳〉,頁649-641。以下凡出自此表者,不復一一標舉頁碼。
[6] 按今本《漢書‧藝文志》著錄者,總計的家數、卷數與此出入不小,實難董理兜合。可參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0),頁260。
[7] 胡楚生:〈隋書經籍志總敘箋證〉,《中國目錄學研究》(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7),頁146,已言及此點。
[8] 〈《七錄》序〉說晉中經為二萬九百三十五卷,但下文已聲明:他當時見到的《中經簿》非完本,「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換言之,二萬九百三十五卷並非西晉中祕的實際收藏量。
[9] 沈約:《宋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四十〈百官志下〉,頁610:「文帝黃初初……祕書改令為監。後欲以何禎【楨】為祕書丞,而祕書先自有丞,乃以禎【楨】為祕書右丞,後省。掌蓺文圖籍」。歐陽詢:《藝文類聚》(臺北:文光出版社,1977),卷五六〈雜文部二‧賦〉,頁1014,所錄《文士傳》云:「青龍元年(233),天子特詔:『楊州別駕何楨有文章才識,使作〈許都賦〉』」。州郡之佐八品,則何楨任六品的祕書丞,必當在此之後。
[10] 《後漢書》,卷七九上〈儒林列傳上‧敘論〉,頁909。范曄加上「石室」。按: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以下簡稱《史記》),卷一三十〈太史公自序〉,頁1336:「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以下簡稱《漢書》),卷一下〈高帝紀〉,頁59:「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後漢書》,卷六一〈黃瓊傳〉,頁722:「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石室」與「金匱」對言,純粹形容其堅固,並非一處所的專稱。
[11] 以上引文分見《後漢書》,卷三七〈桓榮傳附子郁傳〉,頁452,章懷《注》、卷八〈孝靈帝紀‧中平六年〉,頁141。
[12] 樂史:《宋本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三〈河南道三‧河南縣〉,頁31。
[13] 以上引文分見《後漢書》,卷十五〈來歙傳〉,頁223、卷六〈孝順帝紀〉,頁112。
[14] 以上引文分見《後漢書》,卷五〈孝安帝紀‧永初四年〉,頁102,章懷《注》所引《洛陽宮殿名》、卷三五〈曹褒傳〉,頁432。
[15] 盧弼:《三國志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以下簡稱《三國志》),卷六〈董卓傳〉,頁212,裴《注》所引《續漢書》。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一〈送應氏〉之一,頁3:「北登北邙坂,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可資佐證。
[16] 以上引文並見《後漢書》,卷七九上〈儒林列傳‧敘論〉,頁909。
[17] 《後漢書》,卷六一〈黃瓊傳附孫琬傳〉,頁725、卷五七〈李雲傳〉,頁660。
[18] 《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頁1247,《集解》所引如淳曰。
[19] 《漢書》,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敘論〉及《集解》,頁230。曹魏時,此制依舊,故魏文帝薄葬之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見《三國志》,卷二〈文帝紀‧黃初三年〉,頁113。
[20] 《史記》,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傳〉,頁1142。
[21] 以上引文分見《漢書》,卷八十〈宣元六王列傳‧東平思王傳〉,頁1452、卷一百上〈敘傳〉,頁1762。
[22] 《三國志》,卷十九〈陳思王傳〉,頁517。所以會說「副」,因為底本在曹植子孫處。吳士鑑、劉承幹:《晉書斠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以下簡稱《晉書》),卷五十〈曹志傳〉,頁951:「(武)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可資佐證。
[23] 荀勖:〈序〉,王貽樑:《穆天子傳匯校集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2。
[24] 《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附子固傳〉,頁480。
[25] 《後漢書》,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傳‧北海靖王興傳〉,頁210、卷五九〈張衡傳〉,頁689、卷五二〈崔駰傳附孫寔傳〉,頁619、卷八十上〈文苑列傳‧邊韶傳〉,頁935。
[26] 浦起龍:《史通通釋》(臺北:世界書局,1970),卷十二〈外篇‧古今正史〉,頁163。另參《後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傳〉,頁711。
[27] 對照《後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傳〉,頁712:「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舊文」指的應該是這些部分,而且猶非全然不存。至於早先已撰寫完成者,於獻帝時尚完好,否則,《隋書》,卷三三〈經籍志‧史‧正史〉,頁487,怎麼會著錄「起光武記注至靈帝」的一百四十三卷《東觀漢記》?有關《史通》這段話較恰當的理解,詳參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香港:中華書局,1974),卷五〈史部三‧東觀漢記二十四卷〉,頁242-243。
[28] 《後漢書》,卷五四〈楊震傳附曾孫彪傳〉,頁638:「年八十四,黃初六年(225)卒于家」。
[29] 據《三國志》,卷四二〈孟光傳〉,頁862:「古書無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卷五四〈呂蒙傳〉,頁1050,裴《注》所引《江表傳》:「孤……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隋書》,卷三三〈經籍志‧史‧雜史〉,頁490,著錄張溫所撰《三史略》二十九卷,可見:建安年間,南方已有部分《漢記》面世,這大概是祕閣中工作人員私下抄寫,攜出宮外者。從下文所引《典論‧自敘》,可知:當時北方反而尚未睹。從《晉書》,卷四四〈華表傳附弟嶠傳〉,頁874:「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卷八二〈司馬彪傳〉,頁1412:「泰始中,為祕書郎,轉丞」,「以為……漢氏中興,迄于建安……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眾書,綴其所聞」,以嶠、彪的家世,尚待入中祕,始見《漢記》,可見:在北方,此書全稿始終未流佈於外間。
[30]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六藝略‧書‧敘論〉,頁877。
[31] 『孔安國』:〈《尚書》序〉,孔穎達:《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卷一,頁11。
[32] 黃暉:《論衡校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二八〈正說〉,頁1121。《晉書》,卷三六〈衛瓘傳附子恆傳‧四體書勢〉,頁743:「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漢世祕藏,希得見之」。
[33] 《漢書》,卷八八〈儒林列傳〉,頁1550。
[34] 《後漢書》,卷三〈肅宗孝章帝紀‧建初八年〉,頁80:「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卷三五〈鄭玄傳〉,頁433:「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卷三六〈賈逵傳〉,頁444:「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
[35] 《後漢書》,卷二七〈杜林傳〉,頁344。
[36] 這究竟是侯景方面的人焚燒的,還是雙方攻拒時波及,不得而詳,但從李延壽:《南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八十〈賊臣列傳‧侯景傳〉,頁918:「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廚,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可知:蕭梁方面還主動焚書。然姚思廉:《梁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五六〈侯景傳〉,頁407:「至夜,太宗募人出燒東宮,東宮臺殿遂盡」,不及圖書見燬之事;李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以下簡稱《御覽》),卷六一九〈學部十三‧焚書〉,頁2911,所錄《三國典略》更於起火源由作含糊之詞:「(侯景軍士)夜於宮中置酒奏樂,忽聞火起,眾遂驚散」,似皆為蕭綱縱火之舉隱諱。
[37] 《南史》,卷八十〈賊臣列傳‧侯景傳〉,頁926,作「八萬卷」,蓋以成數計。
[38] 《史記》,卷一三十〈太史公自序〉,頁1347。
[39] 《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頁1258、卷六六〈楊敞傳附子惲傳〉,頁1309。
[40] 《三國志》,卷五七〈虞翻傳〉,頁1082,裴《注》所引《虞翻別傳》。
[41] 《後漢書》,卷六一〈左雄傳〉,頁717。這也可以由《三國志》,卷十三〈華歆傳〉,頁398:「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反推:朝廷原來都要考核孝廉在經學方面的家法的。
[42] 以上引文分見《三國志》,卷十一〈王脩傳〉,頁354、卷十六〈蘇則傳〉,頁456,裴《注》所引《魏略》、卷二三〈常林傳〉,頁584,裴《注》所引《魏略‧清介傳》。
[43] 分見《三國志》,卷十六〈蘇則傳〉,頁456,裴《注》所引《魏略》、卷二三〈常林傳〉,頁584,裴《注》所引《魏略‧清介傳》。
[44] 范寧:《博物志校注》(臺北: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卷六〈人名考〉,頁71:「蔡伯喈母,袁公熙妹,曜卿姑也」,對照《三國志》,卷十一〈袁渙傳〉,頁345,裴《注》所引袁宏:《漢紀》,知:公熙乃司徒袁滂之字。《晉書》,卷三四〈羊祜傳〉,頁709:「世吏二千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
[45] 《後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傳〉,頁703、706。
[46] 《蔡中郎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卷九〈巴郡太守謝版〉,頁5b。
[47] 《三國志》,卷二一〈王粲傳〉,頁531。
[48] 《三國志》,卷二八〈鍾會傳附王弼傳〉,頁681-682,裴《注》所引。
[49]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附錄二〉,頁278-279。
[50]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建安五年〉,頁44,記載:官渡之役,袁紹大敗,倉皇北奔,曹方人員「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從下文可知:許多書指的是許昌、軍中人員與袁方私下交通的信件;《晉書》,卷一〈宣帝紀‧青龍元年〉,頁31,記載:諸葛亮卒於五丈原,蜀軍迅速撤軍,司馬懿「獲其圖、書」,從下文可知:乃「軍書密記」、地圖一類,與此處所言的「書」有別。
[51] 《三國志》,卷二〈文帝紀‧黃初七年〉,頁122,裴《注》所引《典論‧自敘》。
[52] 《三國志》,卷二一〈王粲傳〉,頁538,裴《注》所引《魏略》。
[53] 以上引文分見《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建安二五年〉,頁83,裴《注》所引《魏書》、頁84,所引張華:《博物志》、卷首,頁24,所引孫盛:《異同雜語》。
[54] 《三國志》,卷十九〈任城威王傳〉,頁499。
[55] 《三國志》,卷十九〈陳思王傳〉,頁500。
[56] 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8),卷四二〈書中〉所收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頁602。
[57] 《皇覽》編撰完成年代,詳參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三章,(一),頁40-41。
[58] 以上引文分見《三國志》,卷二九〈管輅傳〉,頁702,及頁702、694、693,裴《注》所引《管輅別傳》。
[59] 《三國志》,卷十一〈袁渙傳〉,頁346。
[60] 蔡琰被擄掠年代從沈欽韓:《兩漢疏疏證》(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卷十,頁
[61] 《蔡中郎集》,卷三〈劉鎮南碑〉,頁16b。卷首,頁1b
[62] 杜預:〈《春秋》序〉,孔穎達:《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頁15、16。
[63] 《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列傳‧潁容傳〉,頁922。《隋書》,卷三二〈經籍志‧經‧春秋〉,頁478,題署作《春秋釋例》。
[64] 《三國志》,卷二一〈王粲傳〉,頁533。
[65] 《文選》,卷四二〈書中〉所收曹丕:〈與吳質書〉,頁603。
[66] 以上引文分見《三國志》,卷十五〈司馬朗傳〉,頁441,及裴《注》所引《魏書》、卷二七〈王昶傳〉,頁643,裴《注》所引《任嘏別傳》、卷十三〈王朗傳附子肅傳〉,頁409。
[67] 按其文義,當據徐堅:《初學記》(臺北:鼎文書局,1976),卷十二〈職官部下‧祕書郎第十一〉,頁398,所錄王隱:《晉書》補。
[68] 《御覽》,卷二三四〈職官部三二‧校書郎〉,頁1241,所錄。
[69] 《史通通釋》,卷一〈內篇‧六家‧國語家〉,頁7。
[70] 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80),〈附錄〉,頁1195。
[71] 安井衡:《管子纂詁》(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附錄〉,頁4。
[72]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臺北:鼎文書局,1977),卷首,頁25。
[73] 《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附錄一〉,頁278。
[74] 牛弘認為是「荀勖定魏內經」。
[75] 《晉書》,卷二四〈職官志〉,頁543。
[76]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二六〈職官八‧祕書監〉,頁733。
[77] 據虞世南:《北堂書鈔》(臺北:宏業書局,1974),卷五七〈設官部九‧祕書惣五十五〉,頁236,所錄《晉起居注》,祕書省「署吏四百人」,這自然包括校書郎、主書、主圖、主譜史及大小掾從。曹魏祕書省的編制縱然僅及其半,也實難想像祕書監、祕書丞、祕書郎單線領導那麼多下屬。
[78] 《晉書》,卷二二〈樂志上〉,頁515:「泰始九年(273),光祿大夫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韵」,是以卷三九〈荀勖傳〉,頁802,將「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敘於「(賈)充將鎮關右」之後。賈充外放事在泰始七年(271),詳參卷三〈武帝紀〉,頁72。
[79] 據《三國志》,卷四二〈許慈傳〉,頁861:「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眾學。慈、潛並為學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並參同卷〈郤正傳〉,頁870:「弱冠能屬文,入為祕書吏」、〈孟光傳〉,頁862:「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卷三三〈後主傳〉,頁779:「祕書令郤正……並封列侯」,可知:蜀漢確有祕書此一機構及人員編制。蜀亡之後,所藏圖書當與士民簿領等並入曹魏。從卷三五〈諸葛亮傳〉,頁799-800,所附陳壽:〈上《諸葛氏集》表〉,可知:晉朝會主動「存錄」、命人撰「定」某些蜀人著作。從劉琳:《華陽國志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5),卷十一〈後賢志‧益部〉,頁849:「(陳)壽……撰為《益部耆舊傳》十篇。散騎常侍文立表呈其《傳》,武帝善之」,可知:蜀舊臣也會主動將鄉人之作送入西晉官方。
[80] 《通典》,卷三六〈職官十八‧秩品一‧魏〉,頁992。
[81] 《梁書》,卷三四〈張緬傳附弟纉傳〉,頁241:「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不過,參照《宋書》,卷八七〈蕭惠開傳〉,頁1062:「初為祕書郎,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似仍以三年一任為常例。
[82] 以上引文分見《晉書》,卷三〈武帝紀‧太康七年〉,頁82、姚思廉:《陳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二六〈徐陵傳〉,頁157、令狐德棻:《周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二三〈蘇綽傳〉,頁160、《隋書》,卷十二〈禮儀志七〉,頁150。
[83] 《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附玄孫向傳〉,頁964:「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漢章帝所賜的圖書蓋亦此類。
[84] 《後漢書》,卷三五〈鄭玄傳‧戒子書〉,頁434。卷五九〈張衡傳〉,頁681:「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按:卷七九下〈儒林列傳‧薛漢傳〉,頁918:「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後漢書‧續漢志》,卷七〈祭祀志上‧封禪〉,頁1147:「(建武)三十二年(56)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東漢中祕收錄讖、緯、圖、候等乃無疑之事,是以《漢書》,卷三十〈藝文志‧數術略‧天文〉,頁906,就著錄了「圖書祕記十七篇」——阮孝緒也是將「緯讖部」與「天文部」同置於「術伎錄」之下——《後漢書》,卷六六〈王允傳〉,頁778,也說:「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以從」。
[85] 《隋書》,卷十三〈音樂志‧敘論〉,頁158:「《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佚」。所謂「無復樂書」究竟是指當時中祕根本沒有這方面的書,或者是因為數量太少,省併入他類,不另立子目,不得而詳。縱使是後一情況,那也是荀勖在任時的事,非鄭默的裁斷。
[86] 《文選》,卷四六〈序下〉所收任昉:〈《王文憲集》序〉,頁666,善《注》所引王隱:《晉書》作「錯亂」,措辭未免過當。
[87] 如《三國志》,卷十三〈王朗傳附孫叔然傳〉,頁409,裴《注》、《北堂書鈔》,卷一三六〈服飾部三‧囊八十〉自注,頁632、《漢書》,卷九一〈貨殖列傳〉,頁1575,《集解》、《隋書》,卷十三〈音樂志〉,頁158、孔穎達:《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卷五〈天官‧疾醫〉,頁74,孔《疏》。
[88] 有關汲冢書出土年代,舊史分歧,詳參朱希祖:〈汲冢書考〉,《朱希祖先生論文集》(臺北:九思出版社,1979),頁1507-1509。
[89] 〈汲冢書考〉,《朱希祖先生文集》,頁1599,將「言部」連讀,認為二字蓋衍文,或為「侍中」之誤且倒乙者。按:「侍中…臣矯言」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臣壽等言」同一句例,詳見《晏子春秋集釋》,卷首,頁25、《三國志》,卷三五〈諸葛亮傳〉,頁799,「言」乃敷奏以言之謂。《三國志》,卷五五〈周泰傳〉,頁1058:「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晉書》,卷八五〈何無忌傳〉,頁1458:「以會稽王所部精兵悉配之」,「所部」猶言所統領、麾下,「部」乃「所部」的省語。
[90] 《穆天子傳匯校集釋》,頁1-2。
[91] 《晉書》,卷三〈武帝紀〉,頁84。
[92]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分類篇‧五分法之偶現與四分法之代興〉,頁76
[93] 《御覽》,卷六百一〈文部十七‧著書上〉,頁2836,所錄《三國典略》。
[94] 《三國志》,卷二一〈劉卲傳〉,頁552。
[95] 歐陽詢:〈《藝文類聚》序〉,《藝文類聚》,卷首,頁23。
[96] 對參賈公彥:《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卷三三〈夏官‧職方氏〉,頁498,賈《疏》所引《皇覽》,可知:《越傳》以下都是《皇覽》的文字,並非裴駰的補充。孫馮翼輯:《皇覽》,《百部叢書集成‧問津堂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頁3b,將之悉數刊落,不當。
[97] 《三國志》,卷十九〈陳思王傳〉,頁505,裴《注》。《魯連子》對這件事的記述見《史記》,卷八三〈魯仲連鄒陽列傳〉,頁974,《正義》所引。
[98] 王沈等人的《魏書》曾描述曹沖「容貌姿美」,裴松之就批評:「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詳參《三國志》,卷二十〈武文世王公列傳‧鄧哀王傳〉,頁520,裴《注》。
[99] 以上引文分見《史記》,卷一〈五帝本紀〉,頁20、卷八五〈呂不韋列傳〉,頁996,《集解》所引。
[100] 以上引文分見《御覽》,卷二〈天部‧天部下〉,頁138,所錄;《史記》,卷五〈秦本紀〉,頁98、卷三〈殷本紀〉,頁52、卷一一九〈循吏列傳‧孫叔敖傳〉,頁1246、卷四十〈楚世家〉,頁632,等處《集解》所引。
[101] 敦煌所出編號P,2526的類書殘卷,羅振玉:《永豐鄉人稿》,乙稿〈雪堂校刊群書敘錄‧敦煌本修文殿御覽跋〉,《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臺北:大通書局,1968),頁335-339,以為是《修文殿御覽》殘卷。洪業:〈所謂修文殿御覽者〉,《洪業論學集》(臺北: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2),頁89-94,已指出非是,當為編撰《修文殿御覽》的主要根據:《華林遍略》的殘卷。
[102] 以上引文分見《南史》,卷四〈齊本紀上‧高帝紀‧建元三年〉,頁64、蕭子顯:《南齊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四十〈武帝十七王列傳‧竟陵文宣王傳〉,頁331、《南史》,卷四八〈陸杲傳附子罩傳〉,頁556。
[103]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諸子略‧雜家‧敘論〉及《集解》,頁897。
[104]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頁20,《索隱》:「注:《皇覽》,書名也……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對照《文選》,卷五九〈墓誌〉所收任昉:〈劉先生夫人墓誌〉,頁841,善《注》所引《皇覽‧聖賢冢墓誌》注,可推知:當屬南朝節抄《皇覽》者的註解。將「皇」訓為名詞,乃蹈王逸之誤轍。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卷一〈離騷〉,頁4:「皇覽揆余之初度」,王《注》。
[105] 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外篇一‧立言有本〉,頁202。
[106]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0),卷四〈諸子〉,頁
[107] 杜預:〈後序〉,《左傳注疏》,頁1063。
[108] 《晉書》,卷五一〈束皙傳〉,頁978-9。以下凡出自束皙對汲冢書的概述部分,均見頁977-979,不復一一標明頁碼。
[109] 宋敏求,《唐大詔令集》(臺北:鼎文書局,1972),卷八一〈政事‧經史〉所收〈修晉書詔〉,頁467。
[110] 劉昫:《舊唐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六六〈房玄齡傳〉,頁1193。然以「至(貞觀)二十年,書成」,則非是。
[111] 《史通通釋》,卷十二〈外篇‧古今正史〉,頁167:「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汲冢出書乃武帝時事,所以不可能言及;「佐著作郎束皙又撰十志,會中朝散亂,其書不存」,是以縱使束皙於晉志中曾記載汲冢諸書性質,江左已降諸人皆不得見。對照《藝文類聚》,卷四十〈禮部下‧冢墓〉,頁732,所錄王隱:《晉書》:「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古書。有《易》卦,似《連山》、《歸藏》文;有春秋,似《左傳》」,與〈束皙傳〉相去甚遠,則也當非臧書取材之處。《晉書》,卷八二〈王隱傳〉,頁1414,曾明言:虞預《晉書》乃「竊寫」王隱之作,連帶可知:汲冢諸書的概述也非取材自虞預所撰。
[112] 所以說「初步」,因為〈束皙傳〉轉述的報導對於究竟是誰的冢,還存兩可之說:「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而且還傾向後者,所以會說:「《紀年》……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但荀勖整理完《穆天子傳》,進呈武帝時,已以古籍佐證:「蓋魏惠成子、令【今】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見荀勖:〈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頁1。據《晉書》,卷三〈武帝紀〉,頁81,杜預卒於太康五年(284)閏十二月。他的〈後序〉已經全然確定「今王」指的是魏襄王。可見:這份概述乃早期報告,為王隱《晉書》所據者。
[113] 所以不認為《中經簿》為這段概述的依據,因為按照本文前言所引《隋志》,《中經簿》於著錄的各書「但錄題及言【卷】」,「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
[114] 〈《七錄》序〉說:《中經簿》「其中有十六卷佛經」。《隋志》概述《中經簿》所收書籍性質時,不言及,當是附錄於某子目之下。由此可反推:「汲冢書」非附錄。
[115] 六朝以降的六卷本乃是將同出自汲冢的〈穆王美人盛姬死事〉附加於後。
[116] 《古史考》對此事的辨偽原文已佚,但《史記》,卷四三〈趙世家〉,頁669、670,《索隱》仍簡略撮述了譙周的意見。
[117] 郭璞:〈《山海經》敘〉,《山海經箋疏》,頁592、591。
[118] 楊士勛:《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頁7,范寧:〈《春秋穀梁傳》序〉,及楊《疏》。
[119] 黃伯思:《東觀餘論》,《百部叢書集成初編‧學津討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卷下〈校定《師春書》序〉,頁
[120] 其佚文見洪頤煊輯:《汲冢瑣語》,《百部叢書集成‧問津堂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121]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諸子略‧陰陽家〉,頁893、《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487,《集解》。
[122] 《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頁920。
[123] 《文選》,卷十五〈賦辛‧志〉所收張衡:〈思玄賦〉,頁220,善《注》所引。
[124] 荀勖:〈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頁2。
[125] 杜預:〈後序〉,《左傳注疏》,頁1062。
[126] 黃葵點校:《陸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十〈書集〉,頁176,所附車永:〈又答書〉。「能」改讀為「而」,乃但是、不過之意。二字通假例證詳參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蒸部第二‧能字聲系〉,頁34。
[127] 《史通通釋》,卷十三〈外篇‧疑古〉,頁184。
[128]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史‧起居注‧敘論〉,頁491-492。
[129] 《七錄》已經將「鬼神部」與「國史部」等並列,置於「記傳錄」之下。
[130] 分見《漢書》,卷三十〈藝文志〉,頁890、《隋書》,卷三四〈經籍志三‧子〉,頁508、505。
[131] 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十一〈子類〉,頁506。
[132]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頁37。
[133] '《隋書》,卷七八〈藝術列傳‧萬寶常傳〉,頁890,敘及當時的樂律爭議。萬氏雖是真正的內行,卻屈居少數,當時「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為可以行矣』」,堪為佐證。
[134] 《後漢書》,卷七九上〈儒林列傳‧敘論〉,頁909。
[135] 從《隋志》下文:「及平陳已後……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可知:撰者非不明瞭官方有副本的存在,然仍因循牛弘當時的背景行文,實非允當。
[136]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珍寶部五‧璧〉所錄曹丕:〈蔡伯喈女賦‧序〉,頁3715。
[137]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史‧簿錄〉,頁500。
[138] 牛弘將之壓低為「三萬餘卷」。
[139] 《南史》,卷八〈梁本紀下‧元帝紀‧承聖三年〉,頁118、李百藥:《北齊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四五〈文苑列傳‧顏之推傳‧觀我生賦〉,頁290。《御覽》,卷六一九〈學部十三‧焚書〉,頁2911,所錄《三國典略》,作「十四萬卷」。
[140] 《周書》,卷三二〈唐瑾傳〉,頁231。
[141] 呂才:〈《王無功文集》序〉,金榮華:《王績詩文集校注》(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2。
[142] 《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頁1257。
[143] 張湛:〈《列子》序〉,《列子集釋》,〈附錄二〉,頁279。張湛並沒有註出他祖父的名字,此據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臺北:正文書局有限公司,2000),下卷〈任誕〉,條43,頁680,劉《注》所引《張氏譜》。
[144] 如《北堂書鈔》,卷一百一〈藝文部七‧寫書二十三〉,頁448,自注所引謝承:《後漢書‧孫曄傳》、《三國志》,卷五三〈闞澤傳〉,頁1032、《梁書》,卷三三〈王僧孺傳〉,頁230。
[145] 以上引文分見《後漢書》,卷六二〈荀淑傳附孫悅傳〉,頁733、《三國志》,卷三二〈先主傳‧建安十七年〉,頁759,裴《注》所引《益部耆舊雜記》、卷二一〈王粲傳〉,頁532。
[146] 《梁書》,卷二七〈陸倕傳〉,頁197。
[147] 以上引文分見《晉書》,卷九二〈文苑列傳‧左思傳〉,頁1553、卷五一〈皇甫謐傳〉,頁967;《梁書》,卷三四〈張緬傳附弟纘傳〉,頁241、《周書》,卷四二〈蕭大圜傳〉,頁313。
[148] 《漢書》,卷一百上〈敘傳〉,頁1762、《三國志》,卷三八〈秦宓傳〉,頁831。
[149] 《三國志》,卷四二〈許慈傳〉,頁861。
[150] 如錢仲聯:《鮑參軍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三〈樂府‧松柏篇‧序〉,頁178、《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列傳‧崔慰祖傳〉,頁417、《梁書》,卷四九〈文學列傳上‧袁峻傳〉,頁337。王肅注:《孔子家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695冊,〈後序〉,頁109:「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一般認為這篇〈後序〉乃王肅偽作,但也正可反映:在曹魏當時,出借書本或贈與副本乃常態。